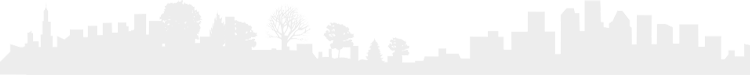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:我的红色家风
清廉奉公守初心
李树屏(1921—1999)原名易功,河北行唐人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参加工作,曾在河北灵寿县、行唐县、察哈尔省宣化市、冀晋四专任小学教员、区助理员、合作社主任、银行总务、区公所副区长、派出所所长等职。1949年7月,在察哈尔省党校进修公安业务。1950年3月后,任大同市一区公安秘书、总务科科长。1952年5月后,先后任大同市劳改大队副大队长、劳改五队副大队长,西峪煤矿矿长,劳改局煤管处副处长、供销处副处长,王庄煤矿矿长,荫营煤矿矿长。1970年7月,在五寨县插队。1973年7月,任晋普山煤矿矿长。1985年离休。
讲述人:李敬苗 李东翔 讲述时间:2023年2月16日 整理人:江雪
风里浪里干革命
又是一年春节,打扫家里卫生,拂拭一幅幅照片,我们又看到了父亲——他的微笑让人感觉那么温暖。
二十三年了,每到春节一家人团聚时,年迈的母亲就会嘱咐我们,先给你们爸爸摆上碗筷——我们还像小时候等父亲回家吃饭一样,给父亲盛好饭,等父亲带着一肩雪花回来……
1921年初冬,我们的父亲李树屏出生在河北省行唐县一个贫农家庭。家里有爷爷、奶奶和父亲兄妹四个,六口人仅靠不足一亩的薄地维持生活。好在爷爷从小学了银匠手艺,农闲时便走街串巷,为有钱人家的小姐打耳环、戒指什么的补贴家用。父亲七八岁时,爷爷便带着他,挑着担子到附近的村镇,招揽些银匠活计。有一天,父子俩走到灵寿县西岔头村招揽活计,不禁被这里的环境和当地的生活物资交易市场的繁华所吸引。灵寿县历史悠久,滹沱河从这里缓缓流过。雄伟的太行山与美丽的滹沱河,山河携手、交相辉映,汇聚成了别样风光。爷爷看到这里山川秀美,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比老家好,就把家里人接过来,想在这里立足。但那个年代,军阀混战,土匪骚扰,国民党搜刮民膏民脂……一家人在西岔头村的日子并没如爷爷所愿变得好起来,反而过得更加艰难。
西岔头村南有一条山路,紧靠滹沱河的支流——终年川流不息的磁河。河边芦苇浩荡,夏日碧绿万顷,随风起伏,一眼望不到边。当时农村建房屋都需要用芦苇苫盖屋顶,所以这片芦苇便成了当地百姓的“钱袋子”。更重要的是,在抗战时期,浩荡的芦苇荡还为我党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。面对日军突然来“扫荡”,当地老百姓便会划一艘小船躲藏进芦苇荡中;我党很多地下工作也在这里秘密开展。西岔头村南那条路上通京津,下达石家庄。日军从灵寿县城出来到解放区扫荡,必经此路。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躲在芦苇荡中,将路过的日军有多少人、多少枪、多少车辆等情报及时且准确地传递给八路军、武工队。
当时,西岔头村逢三、五、七就有集市贸易交流会,我地下党便抓住集会人多方便的优势,在这里发动群众,宣传党的政策,召开各种会议。七七事变后,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,父亲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,193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9年便担任了抗日区小队队长。在武工队的领导下,他带领区小队的同志们,站岗放哨、送情报,组织民兵武装、妇救会、儿童团,配合主力部队同侵华日军开展了一次次的游击战。他们经常深入敌后,到灵寿县城党的地下交通站取送情报,乔装打扮成普通农民到鬼子炮楼侦查情况,了解敌人炮楼的战备布置和人员信息,然后把情报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。日军“扫荡”时,得到情报的小分队便立即行动,组织村民向安全的地方转移。安顿好村民,他们便开始埋地雷,并用土枪、手榴弹等配合主力部队与日军作战。没有战斗的时候,他们就成了村里的工作队、生产队,斗地主、除恶霸、分田地,搞生产互助、减租减息,组织民兵担架队,组织妇女们做军鞋军衣,做干粮、炒炒面,支援前线,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
抗战后期,由于工作需要,接受党组织安排,父亲秘密回到行唐老家,当了一名小学教员。父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,只断断续续在农闲时学了一点儿文化。但他服从组织命令,克服重重困难,认认真真地做起了“先生”。父亲在教员身份的掩护下,发展党员,发动群众共同抗日。后来,父亲在组织的安排下,还担任过区助理员、合作社主任、银行总务、区公所副区长,派出所所长等职务。
忠诚为党守初心
1949年7月,父亲接到任务,到当时的察哈尔省党校进修公安业务。培训结束,按照组织安排,父亲跟随部队南下;刚走到大同,忽然又接到上级命令,让他们支援当地工作——就这样,父亲被分配在大同公安局,先后任大同市一区公安秘书、市局总务科科长。1952年,察哈尔省撤销,大同划归山西省。
父亲说,让他终生难忘的任务是那次极艰难的迁移。当时,山西省公安劳改系统机构重组,决定把大同看守所在押罪犯全部迁移到太原西峪煤矿。那是一次特别艰难的迁移,也是一次特别危险的迁移。这支迁徙队伍的主要成员是罪犯,这些罪犯中有国民党战犯、特务,有社会渣滓,还有政治反革命、刑事犯等——很多罪犯是仇视新中国的敌对分子,一旦出意外,后果不堪设想。临出发前,父亲和参与押送的工作人员反复推敲讨论迁移行动的每一个细节。经过缜密的安排部署,父亲和武警战士、监狱干警以及工作人员一起,押着罪犯,用马车拉着行李,徒步前往西峪煤矿。那时候别说高速公路,就连普通公路也没有。从大同到太原有七八百里的山路,父亲和他的同事们,过朔县、代县、雁门关……一路风萧萧雨潇潇,黄沙漫天,他们不仅饱受风餐露宿、穿山越岭之苦,还必须时时刻刻从思想上绷紧弦,警惕罪犯逃逸、造反。父亲他们凭借对党的忠诚和周密的工作部署,终于按预定时间安全到达目的地,所有工作人员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此后,在党中央的部署下,西峪煤矿监狱的干警们白手起家,经过不断摸索,不断总结经验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使西峪监狱的工作走向正轨。20世纪50年代初,新中国的监狱改造工作刚迈开步子,正处于探索、摸索阶段。改造和生产双驱并进是我们国家改造罪犯的路线、措施和手段。父亲爱学习、爱钻研,到监狱工作后,很快便掌握了煤炭行业的开采技能,并琢磨了一套管理办法。煤矿的有序生产,既解决了监狱的各项开支,又给国家上缴了利润,同时也开创了监狱工作的新局面。监狱、煤矿双驱并进,父亲他们在新中国建设的战线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。
1956年,父亲被组织选送到中国地质大学进修。学成归来,父亲成为山西省监狱系统四大煤矿生产的主要领导。
煤矿安全,是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,不得有半点侥幸和疏忽的心理。父亲他们制定了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,做到布置、检查、落实到位,单位领导干部按规定每天必须有一个人带班,现场及时解决问题。父亲是出了名的“黑脸包公”,对违规者,坚决不留情面,按制度给予处罚。父亲曾说,“煤矿生产,安全问题大于天,因为煤矿人命关天,一旦出错,可能就会酿成大错。只有把紧安全关,才能尽量不出问题”。
父亲是搞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老党员,他的党性宗旨很强,工作纪律性也很强。在我们的记忆里,父亲总是只说上班不说下班,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,更别说调休和轮休。他每天早早就离家上班、开会、外出,决不迟到一分钟。但到了下班时间,经常看不到父亲回家的影子。那时候我们家吃饭的规矩——父亲下班没回来,母亲就不让开饭。有时候眼看等的都快到上学时间了还等不来父亲,母亲才无奈下令开饭。很多次,父亲好不容易回来了,刚端起碗就有人来谈工作,他只好把碗放下。逢年过节,他不是下坑就是去监房,很少在家。
父亲从参加工作到离休,时时处处以一个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但他从来没有当过一次先进或模范,并不是父亲不够条件,而是因为他见荣誉就让,见困难就上,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。那时候矿井条件不好,有些地方开采没有到位,人需要爬着过去,父亲总是第一个爬过去。由于父亲身材魁梧,在一次爬行中,锋利的煤块磕到了他的肋骨,父亲骨折了。但即使骨折,他还是一天也不休息。
正因为有父亲这样忠诚无私的一代人,监狱改造、生产的双重任务才能很好地完成。1975年,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煤炭系统代表,父亲作为全国煤炭系统代表赴北京参加了那次接见。那是父亲一生的荣耀,回来后,他难抑激动,把长长的照片在家里摆放了一张,还在办公室摆放了一张。那张照片伴随了他一生,那份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也伴随了他一生。
清正廉洁一辈子
父亲是穷人家出身,他与他们那代人一样,把艰苦朴素当作了生活的法宝。我们记得,那时候父亲穿的衣服,膝盖部位、肘关节部位总是打着补丁。按说,他的衣服破了,是可以领新的穿的。但他总是只领两套工作服,办公室一套,家里一套。至于工作用品都是需要了才领,不用就不领。父亲工作几十年,从来没有往家里拿回过单位的一张纸,甚至一个钉子……在饮食上,父亲把对粮食的爱惜做到了极致。他不挑食,更见不得一点儿浪费。吃饭的时候,我们一旦把饭粒掉在饭桌上,父亲就用筷子敲敲桌面,提醒我们把掉的饭粒捡起来吃掉。父亲不会说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但他常常吓唬我们说,“谁糟蹋一粒粮食,老天爷都会看到,就会惩罚这个人”。我们认真地问父亲:“老天爷怎么惩罚这个人啊?”父亲就一本正经回答:“老天爷会让那个人挨饿,吃不上饭;若是太不像话了,老天爷还会发威,大旱大涝或者地震,田地荒芜,收不上粮食。”父亲的话无疑对年幼的我们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。后来,我们也养成了习惯,一旦掉落饭粒赶紧捡起来吃掉。父亲的这一做法影响了我们,我们又影响了下一代。我们长大后,知道一粒米饭并不足以让“老天爷”发威,但几十年的习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。现在虽然生活富足了,但我们从来不会浪费粮食。
20世纪70年代,年轻人流行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那是一种时髦。当时,我们也都想要一身发白的工作服,就与父亲商量说:“能不能给我们拿一身回来,让我们也赶一下流行?”谁知父亲一听,脸立即黑了下来,他非常严厉地训斥道:“你们穿上像什么呢?那是国家给工作人员穿的,你们穿了算什么!”看着父亲,我们只能硬生生把委屈吞下去,谁让我们有这样一位坚持原则、清廉奉公的父亲呢!有一次,听父亲单位管劳保用品的师傅说,你父亲的劳保用品领得最少,本来应该领走的,他都以“不需要”为由一直没有领,包括口罩、肥皂。别人是想法多领,你父亲是本来应该领的,却没有领走。
那时,以父亲的职位,为亲戚安排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,但父亲始终没有把手中的那点“权”用在私人关系上,但是他对待有困难的同志和家属,却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困难。那时候,单位每年有百分之二的自然减员指标。为解决家庭真正有困难的人,父亲不怕得罪人,把指标分配给了真正困难的同志。一些接受过父亲帮忙的同事,拿一些烟酒或土特产来家感谢他,父亲都一概婉言谢绝。
20世纪70年代,国家号召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,父亲积极带头,我们姊妹三个从学校刚毕业,就被他安排到农村插队去了。其实,按照当时的政策,每家可以留下一个子女参加工作;父亲给别人家是按照政策办理,留下一个孩子,帮人家孩子安排工作。我们到了结婚年龄,国家号召晚婚晚育,父亲又要求我们响应国家政策。因此我们姐妹结婚,都在晚婚晚育规定范围之内。我们曾对父亲的做法很不满意,但父亲说:“我是共产党员,共产党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,共产党员就意味着不能谋私,不能让群众说长道短。”
从我国第一次确定干部工资起,父亲的工资档次一直没有升。改革开放后,国家多次给工作人员调级涨工资;但父亲说,他的工资国家已经给得够高了,好多拖家带口的职工比他困难多,所以他不争,要把机会让给困难的同志。
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,他用一生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他始终把忠诚党的事业贯穿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上。在工作的几十年中,父亲批评的人、处罚的人、处理的人很多,但父亲的公平公正、清正廉明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赞扬。
父亲还有很多美德,比如谦恭礼让、勤劳朴实、做事硬气、坦荡无私,他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。我们兄妹六人,有三个入了党,并多次在单位获评优秀党员、先进工作者或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。
父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,但他兢兢业业工作、清正廉洁为人的好作风在我们家传了下来。我们一定会把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传承下去,让我们的后代忠诚于党的事业,做清白的、勤奋的、遵纪守法的老实人,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量。
摘自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——我的红色家风》